![图片[1]-在家副业女生怎么称呼她 坐在杏树下,环视群山,感觉明亮的道理-侠客笔记](https://qiniu.uuwangluo.cn/mfxm/20241107/e3a32080504517f173f1eaaf5c857fe4_0.png?imageView2/0/format/webp/q/75)
本文是徐冰回忆自己七十年代在京郊农村插队往事的文章,节选自活字文化“视野丛书”之《我的真文字》(中信出版社)里的第一篇《愚昧作为一种养料》。徐冰的知青生涯被他自己称为“一段愚昧的历史”,他所处的燕北山区远离七十年代政治中心,单调、贫瘠,一片灰蒙蒙。不过,徐冰却写出了一篇非常好看的文章,二勤子的故事、读《毛选》的体验、李先生的悲剧让人过目不忘。历史的宏大叙事再精彩,仍不如一个个小人物的际遇来得惊心动魄。
![图片[1]-在家副业女生怎么称呼她 坐在杏树下,环视群山,感觉明亮的道理-侠客笔记](https://qiniu.uuwangluo.cn/mfxm/20241107/e3a32080504517f173f1eaaf5c857fe4_0.png?imageView2/0/format/webp/q/75)
![图片[3]-在家副业女生怎么称呼她 坐在杏树下,环视群山,感觉明亮的道理-侠客笔记](https://qiniu.uuwangluo.cn/mfxm/20241107/e3a32080504517f173f1eaaf5c857fe4_2.jpg?imageView2/0/format/webp/q/75)
徐冰在花盆公社,1975
1972 年邓小平复职,一小部分人恢复上高中。由于北大附中需要一个会美工的人,就把我留下上高中。邓的路线是想恢复前北大校长陆平搞的三级火箭——北大附小→北大附中→北大附中高中→北大。但没过多久,说邓搞复辟,又被打下去。高中毕业时,北大附中、清华附中、一二三中的红卫兵给团中央写信,要求与工农划等号,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此信发在《光明日报》上(后来才知道这是团中央某人授意的),形成了最后一个上山下乡的小高潮。我们选择了北京最穷的县、最穷的公社去插队。由于感激学校留我上高中,我比初中时更加倍为学校工作,长期熬夜,身体已经很差了——失眠、头疼、低烧。只好把战友们送走了,自己在家养病。半年后似乎没事了,办了手续,去找那些同学。我被分到收粮沟村,两男三女,算是村里的知青户。
这地方是塞北山区,很穷。那年村里没收成,就把国家给知青的安家费给分了,把猪场的房子给我们住。这房子很旧,到处都是老鼠洞,外面一刮风,土就从洞中吹起来。房子被猪圈包围着,两个大锅烧饭和熬猪食共用。深山高寒,取暖就靠烧饭后的一点儿炭灰,取出来放在一个泥盆里。每次取水需要先费力气在水缸里破冰:至少有一寸厚。冬天出工晚,有时我出工前还临一页《曹全碑》,毛笔和纸会冻在一起。我是4 月份到的,冬天还没过,这房子冷得没法住,我和另一个男知青小任搬到孙书记家。他家只有一个大炕,所有人都睡在上面。我是客人被安排在炕头,小任挨着我,接下去依次是老孙、老孙媳妇、大儿子、二儿子、大闺女、二闺女,炕尾是个弱智的哑巴。这地方穷,很少有外面的姑娘愿意来这里;近亲繁殖,有先天智障的人就多。这地方要我看,有点像母系社会,家庭以女性为主轴,一家需要两个男人来维持,不是为别的,就是因为穷的关系。明面上是共产党的一夫一妻制,但实际上有些家庭是:一个女人除了一个丈夫外,还有另一个男人。女人管着两个男劳力的工本,这是公开的。如果哪位好心人要给光棍介绍对象,女主人就会在村里骂上一天:“哪个没良心的,我死了还有我女儿……”好心人被骂得实在觉得冤枉,就会出来对骂一阵。如果谁家自留地丢了个瓜什么的,也会用这招把偷瓜的找出来。
村里有大奶奶、二奶奶、三奶奶、四奶奶,我好长时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后来在一个光棍家住了一个冬天,才知道了村里好多事。收粮沟村虽然穷,但从名字上能看出,总比“沙梁子”“耗眼梁”这些村子还强点儿。收粮沟过去有个地主,土改时被民兵弄到山沟用石头砸死了,土地、房子和女人就被贫下中农给分了,四个奶奶分给四个光棍。搞不懂的是,这几个奶奶和贫下中农过得也挺好,很难想像她们曾是地主的老婆。那年头,电影队一年才出现一次,可在那禁欲的年代,这山沟里在性上倒是有些随意:一个孩子越长越像邻居家二叔了,大家心照不宣,反正都是亲戚。
我后来跟朋友提起这些事,会被追问:“那你们知青呢?”我说:“我们是先进知青点,正常得很。”一般人都不信。现在想想,先进知青点反倒有点不正常,几个十八九岁的人,在深山,完全像一家人过日子。中间是堂屋,左右两间用两个布帘隔开,我和小任在一边,三个女生在另一边。有时有人出门或回家探亲,常有只留下一男一女各睡一边的时候。早起,各自从门帘里出来,共用一盆水洗脸,再商量今天吃什么。看上去完全是小夫妻,但绝无生理上的夫妻关系。
![图片[4]-在家副业女生怎么称呼她 坐在杏树下,环视群山,感觉明亮的道理-侠客笔记](https://qiniu.uuwangluo.cn/mfxm/20241107/e3a32080504517f173f1eaaf5c857fe4_3.jpg?imageView2/0/format/webp/q/75)
收粮沟村写生,1974
我十八九岁那阵子,最浪漫的事可借此交代一二。穷山出美女,这村里最穷的一户是周家。老周是个二流子。老周媳妇是个谦卑的女人:个子有点高,脸上皱纹比得上皱纹纸,但能看出年轻时是个美女。整天就看周家忙乎,拆墙改院门,因为他家的猪从来就没养大过,所以家穷。按当地的说法,猪死是院门开得不对。老周的大女儿二勤子是整个公社出了名的美女。我们三个女生中,有一个在县文工团拉手风琴,她每次回来都说:“整个文工团也没有一个比得上二勤子的。”二勤子确实好看,要我说,这好看是因为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多好看。二勤子说话爱笑,又有点憨,从不给人不舒服的感觉,干活又特麻利,后面拖一根齐腰的辫子,这算是她的一个装饰。一年四季,这姑娘都穿同一件衣服,杏黄底带碎花,天热了,把里面棉花取出来,就成了一件夹衣,内外衣一体。天冷了,再把棉花放回去。
二勤子家正对学校小操场。有一次有点晚了,我斜穿小操场回住处,有人在阴影处叫我“小徐”,村里人都这么称呼。我一看,是二勤子坐在她家院门围栏上,光着上身,两个乳房有点明显。我不知所措,随口应了声“哎,二勤子”,保持合适的速度,从小操场穿了过去。第二天上工,二勤子见到我说:“我昨晚上把衣服给拆洗了,天暖了。”每逢这时节,她在等衣服晾干时,家里也有人,她在哪儿呆着都不方便。
后来知青纷纷回城了。一天二勤子来找我,说:“小徐,你帮我做一件事行不?你常去公社,下次去你能不能帮我把辫子拿到公社给卖了?我跟我爹说好了,我想把辫子剪了。”我说:“剪了可惜了。”她说:“我想剪了。”我说:“你怎么不让你哥帮你。”她说:“我不信他,我信你。”几天后,她就拿来一条又黑又粗的辫子,打开来给我看。我第二天正好要去公社办刊物,书包里装着大辫子,沉甸甸的,头发原来是一种很重的东西。我忘了这条辫子卖了多少钱,总之我把钱用包辫子的纸包好,带回村交给她。这点钱对她太重要了,是她唯一的个人副业。
下面再说点和艺术有关的事。可以说,我最早的一次有效的艺术“理论”学习和艺术理想的建立,是在收粮沟对面山坡上完成的。山上有一片杏树,是村里的一点副业。看杏林容易得罪人,队里就把我派去。那年夏天这山坡成了我的天堂。首先,每天连一个杏都不吃——获得自我克制力的满足。再者是专心享受自然的变化。我每天带着画箱,带着书上山,可还没几天,就没什么书好带了,有一天,只好拿了本《毛选》。毛的精彩篇章过去背过,熟到完全感觉不到内容的程度。
可那天在杏树下,读《毛选》的感动和收获,是我读书经验中少有的,至今记忆犹新。一段精彩的有关文艺的论述,是从一篇与艺术无关的文章中读到的:
![图片[5]-在家副业女生怎么称呼她 坐在杏树下,环视群山,感觉明亮的道理-侠客笔记](https://qiniu.uuwangluo.cn/mfxm/20241107/e3a32080504517f173f1eaaf5c857fe4_4.png?imageView2/0/format/webp/q/75)
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方针,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,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。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,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。利用行政力量,强制推行一种风格,一种学派,禁止另一种风格,另一种学派,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。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,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,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,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。
![图片[5]-在家副业女生怎么称呼她 坐在杏树下,环视群山,感觉明亮的道理-侠客笔记](https://qiniu.uuwangluo.cn/mfxm/20241107/e3a32080504517f173f1eaaf5c857fe4_4.png?imageView2/0/format/webp/q/75)
今天重读,真不明白那天对这段话怎么那么有感觉,也许是由于这段话与当时文艺环境的反差。我的激动中混杂着觉悟与愤慨:毛主席把这种关系说得这么清楚、这么有道理,现在的美术工作者怎么搞的嘛!坐在杏树下,我看几句,想一会儿,环视群山,第一次感觉到艺术事业的胸襟、崇高和明亮的道理。那天的收获,被埋藏在一个业余画家的心里,并占据了一块很重要的位置。
北大在郊区,身边的人与美术圈没什么关系,我很晚才通过母亲办公室同事的介绍,认识了油画家李宗津先生,这是我上美院之前求教过的、唯一的专业画家。李先生住北大燕南园厚墙深窗的老楼,他拿出过去的小幅油画写生给我看,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油画魅力。李先生觉得我能看进去,又拿出两张大些的画,有一张“北海写生”是我在出版物上看到过的。在他那里的时间,像是一个没有“文 革”这回事的、单独的时空段,它与外面热闹的美术创作无关,是秘密的,只在那种古老教堂的地下室,只在牧师与小修士之间才有的。
在农村晚饭后,我常去老乡家画头像。画好了,把原作拍张照片送给他们。那批头像有点王式廓的风格,我手边有一本《王式廓素描选》。他善画农民肖像。由于范本与所画对象极为吻合,我的这批画画得不错。只是由于灯光昏暗(一盏灯挂在两屋之间),大部分画面都比较黑。
![图片[7]-在家副业女生怎么称呼她 坐在杏树下,环视群山,感觉明亮的道理-侠客笔记](https://qiniu.uuwangluo.cn/mfxm/20241107/e3a32080504517f173f1eaaf5c857fe4_6.jpg?imageView2/0/format/webp/q/75)
收粮沟农民肖像写生,1977
每次回京,我带着画去看李先生。有一次,他家小屋里挂着一张巨幅油画,顶天立地。原来这是他的代表作《飞夺泸定桥》,从历史博物馆取回来修改。他鼓励我多画肖像画。可那次回村后,上年纪的人都不让我画了。后来才知道,我回京这段时间,四爷死了,走前刚画过他,说是被画走了。反正全村人差不多都画遍了,我后来以画风景为主。
去李先生那里加起来不过三次,最后一次去,怎么敲门也没人应。后来问人才知道,李先生前几天自杀了。原来,他一直带着右派帽子。过去在中央美院,反右后被贬到电影学院舞美系。“文 革”期间不让这类人画画,最近松动些,可以画画了,却又得了癌症。他受不了这种命运的捉弄,把那张代表作修改了一遍就自杀了。那时受苏联的影响,流行画色彩小风景。每次画我都会想到李先生的那几幅小油画;那些逆光的、湿漉漉的石阶,我怎么也画不出那种感觉。
当时有个说法:“知识青年需要农村,农村需要知识青年。”如何发挥知识的作用,是需要动用智慧和知识的。知青中,有的早起去各家收粪便,做沼气实验;有的翻书,研制科学饲料。这很像报纸上先进知青的事迹,难怪,后来我们也成了先进知青。
![图片[8]-在家副业女生怎么称呼她 坐在杏树下,环视群山,感觉明亮的道理-侠客笔记](https://qiniu.uuwangluo.cn/mfxm/20241107/e3a32080504517f173f1eaaf5c857fe4_7.jpg?imageView2/0/format/webp/q/75)
题头尾花剪报本,1972—1973
我能干的就是出黑板报。村里上工集合处,有一块泥抹的小黑板,黑色退得差不多没了,我原先以为是山墙上补的块墙皮呢。有一天我心血来潮,用墨刷了一遍,随便找了篇东西抄上去,重点是显示我的美工才能。完成后,煞是光彩夺目(当时还没抢眼球的说法),从老远的山上,就能看见这鲜亮的黑方块,周边更显贫瘠苍凉。后来,收粮沟一个知青出的黑板报,被人们“传颂”了好一阵。有一次我买粮回来,就听说:“北京有人来看咱村的黑板报了,说知青文艺宣传搞得好。”我后来跟公社的人打听,才知道来者是刘春华,他画了《毛主席去安源》,是当时的北京市文化局局长或副局长。
后来,黑板报发展成了一本叫《烂漫山花》的油印刊物。这本刊物是我们发动当地农民和知青搞文艺创作的结晶。我的角色还是美工,兼刻蜡纸,文字内容没我的事,同学中笔杆子多得很。我的全部兴趣就在于“字体”——《人民日报》《文汇报》这类大报的字体动向;社论与文艺版字体、字号的区别。我当时就有个野心,有朝一日,编一本《中国美术字汇编》。实际上,中国的字体使用,是有很强的政治涵义的,“文革”期间更是如此。可我当时并没有这种认识,完全是做形式分类——宋体、老宋、仿宋、黑宋、扁宋、斜宋的收笔处是否挑起,还有挑起的角度、笔划疏密的安排,横竖粗细的比例。我当时的目标是用蜡纸刻印技术,达到《解放军文艺》的水平。在一个小山沟里,几个年轻人,一手伸进裤裆捏虱子,一手刻蜡纸,抄写那些高度形式主义的豪迈篇章。《烂漫山花》前后出过八期。创刊号一出来,就被送到“全国批林批孔可喜成果展览”中。现在,这本刊物,被视为我早期的作品,在西方美术馆中展出。不是因为“批林批孔”的成果,而是作为蜡纸刻印技术的精美制作。
![图片[9]-在家副业女生怎么称呼她 坐在杏树下,环视群山,感觉明亮的道理-侠客笔记](https://qiniu.uuwangluo.cn/mfxm/20241107/e3a32080504517f173f1eaaf5c857fe4_8.jpg?imageView2/0/format/webp/q/75)
《烂漫山花》对页,1975
一个人一生中,只能有一段真正全神贯注的时期。我的这一时期被提前用掉了,用在这不问内容只管倾心制作的油印刊物上了。
后来我做了不少与文字有关的作品,有些人惊讶:“徐冰的书法功底这么好!”其实不然,只不过我对汉字的肩架结构有很多经验,那是“文 革”练出来的。
『 我 的 真 文 字 』
![图片[10]-在家副业女生怎么称呼她 坐在杏树下,环视群山,感觉明亮的道理-侠客笔记](https://qiniu.uuwangluo.cn/mfxm/20241107/e3a32080504517f173f1eaaf5c857fe4_9.jpg?imageView2/0/format/webp/q/75)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END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限 时 特 惠: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,一年会员只需168元,专属会员社群,免费资源无限下载,每周更新会员专属资源 点击查看详情
站 长 徽: JDXB1111111
本站收集的资源仅供内部学习研究软件设计思想和原理使用,学习研究后请自觉删除,请勿传播,因未及时删除所造成的任何后果责任自负。
如果用于其他用途,请购买正版支持作者,谢谢!若您认为「LPWK168.COM」发布的内容若侵犯到您的权益,请联系站长邮箱:1352181545@qq.com 进行删除处理。
本站资源大多存储在云盘,如发现链接失效,请联系我们,我们会第一时间更新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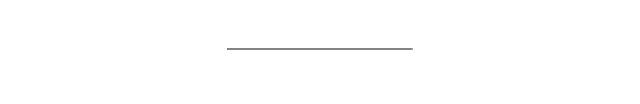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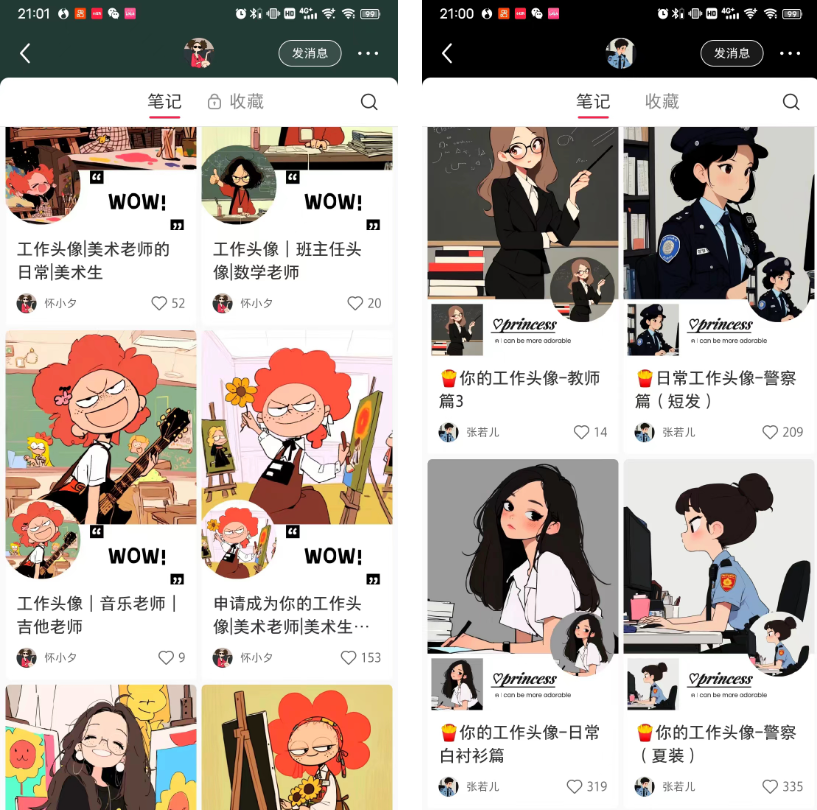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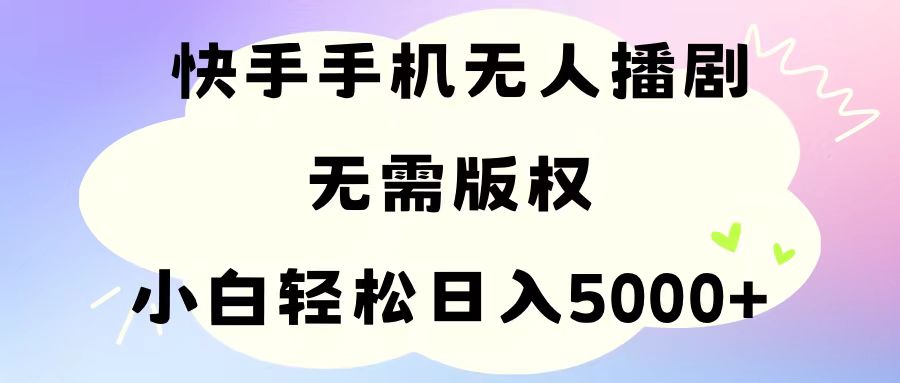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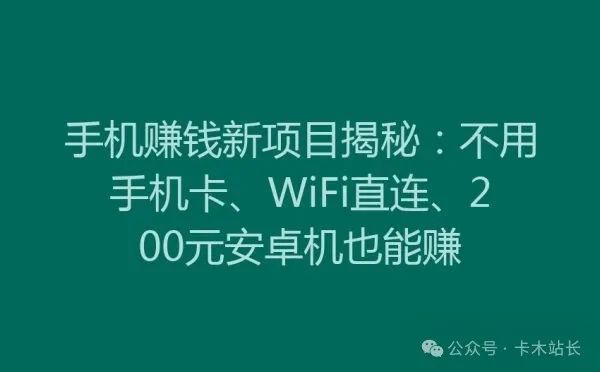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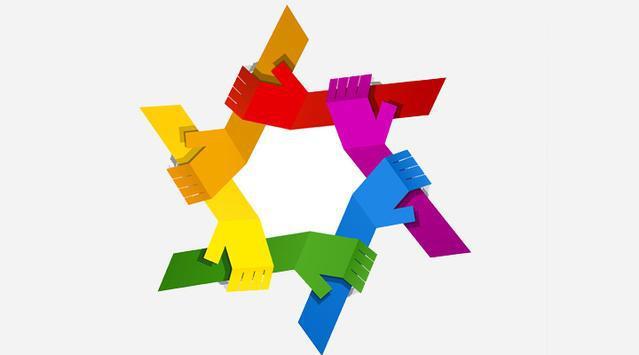


暂无评论内容